- 股票配资平台线上app A50ETF华宝(159596)半日涨幅0.21%,成交额1.16亿元,机构
- 热点栏目 自选股 数据中心 行情中心 资金流向 模拟交易 客户端 8月9日,A50ETF华宝(159596)半日涨幅0.21%,成交额1.16亿元。十大重仓股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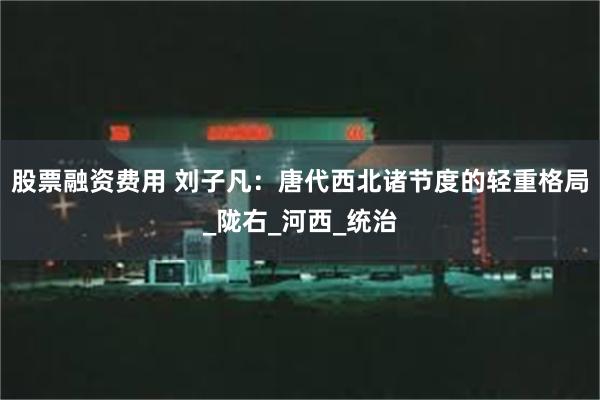
敦煌阳关(图源:视觉中国)
唐朝是一个幅员辽阔的王朝,特别西北边疆延伸至欧亚大陆腹地,自长安至安西四镇最西面的疏勒大致有八千里之遥。唐廷如何管理如此庞大的国家,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以往学者多将唐代的天下秩序总结为同心圆结构,自内向外形成不同圈层,代表着不同的统治方式和逐层递减的统治力度。这一理想化模型大致可以反映唐人的统治观念,然而在政治实践中又会有具体的制度设计,即便是看似同一圈层的统治方式,也会有因地制宜与因时制宜的权变,这些变化中蕴含着唐代维护边疆稳定的关键因素。从唐代西北诸节度的关系入手,或可窥其大略。
唐玄宗时期以节度使为核心的边疆治理体系逐步定型,有所谓“天宝十节度”之说。节度使源自军事使职,皆是直接对皇帝负责,史书中似也未明确记载各节度之间的等级差异,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各节度之间还是有轻重之别。在长安西北的诸节度中,安西、北庭节度使与陇右、河西节度使的军政地位有明显的不同。王永兴提出,河西节度使为西北军事格局的总部,安西节度、北庭节度乃河西节度西向发展之南北两翼;或者说河西节度乃军事财赋之后方根据地,安西、北庭乃其南北两方面之前沿军事据点。李文才也指出,开元二十一年(733)后的十节度中,河西、陇右、朔方三节度使取得最为重要的军事地位。这是对节度使时代唐朝西北格局的重要概况。不过关于西北诸节度使轻重格局的表现、成因与作用,都值得在唐代边疆治理的视野下进一步讨论。本文试以关系较为密切的河陇与西域地区为例,分析诸节度的轻重格局,并管窥唐代实现广阔疆域治理的一些制度特点。
展开剩余93%一、河陇与西域两大军事区域的形成
唐代的陇右、河西、北庭、安西等四镇节度使,都是在陇右道的地域范围内形成,这在天宝十节度中绝无仅有。若要梳理诸节度之间的关系,便需明确这一地区从一道监管到数镇分立的治理变化与布局调整。
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因山川形便,分天下为十道”,其中便有陇右道。大致自陇山(今甘肃六盘山)以西皆是陇右道管辖范围,即所谓“自陇而西,尽其地也”。实际上陇山南北也有所区隔,唐代将陇山以南划入陇右道,以北的原州、灵州则划入关内道,日后的朔方节度使驻地就在灵州。陇右道在设立之初仅西到沙州(今甘肃敦煌),但随着唐朝势力的不断西进,陇右道的控制范围也逐渐扩展。贞观十四年(640)唐廷灭高昌,在天山东部地区建立起以伊州、西州、庭州为核心的军政体系;贞观二十三年(649)击破龟兹,高宗显庆三年(658)平定西突厥阿史那贺鲁,在天山以南的绿洲国家建立起以安西四镇为核心的统治秩序。唐朝的实际管辖范围已延伸到葱岭(今帕米尔高原),而自陇山以西的疆土,便都在陇右道的辖下。即便诸道起初并无固定职官,只是由朝廷不定期派遣官员巡查,陇右道如此辽阔的范围仍然不易监理。于是在唐中宗景云二年(711),陇右道被分为河西、陇右两道。《唐会要》载:“出使者以山南控带江山,疆界阔远,于是分为山南东、西两道。又自黄河已西,分为河西道。”虽然此后河西、陇右作为监察区分合不定,但毕竟开始改变由陇右一道控带山川的格局。
与这一变化同步的是边疆统治方式的制度性变革,即节度使的出现。《通典·职官典》载:
自景云二年四月,始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其后诸道因同此号,得以军事专杀。行则建节,府树六纛,外任之重莫比焉。
大致自高宗以来,唐朝对周边的策略转向守势,逐渐在边疆屯驻重兵,形成分区防守的军区。节度使制度的确立代表着这一调整的定型,而河西节度使正是唐代正式设立的第一个节度使,此前娄师德、唐休璟、郭元振曾先后出任陇右诸军州大使,就是河陇地区节度使的雏形。不过关于河西节度使设立的时间尚有争议,《资治通鉴》卷210唐睿宗景云元年(710)载:“置河西节度、支度、营田等使,领凉、甘、肃、伊、瓜、沙、西七州,治凉州。”《新唐书·方镇年表》亦在景云元年下记载“置河西诸军州节度、支度营田督察九姓部落、赤水军兵马大使,领凉、甘、肃、伊、瓜、沙、西七州,治凉州”。濮仲远据明代重刻唐《凉州卫大云寺古刹功德碑》的记载,提出司马逸客于景云元年便出任河西诸军节度大使,为首任河西节度使。无论如何,河西节度使正是在景云初年设立,与睿宗将陇右道分为河西、陇右两道几乎同时期,体现了河陇地区统治秩序的调整。
唐朝在西北边疆的统治面临着吐蕃、突骑施、突厥等周边政权的挑战,河西节度使显然无力独自完成镇守陇右道与河西道广阔疆土的职责,据上引《资治通鉴》与《新唐书》,河西节度使设立之初的统辖范围包括河西走廊与西域东部的西州、伊州,未及陇右及安西。故而在唐玄宗初年,原陇右道地区又先后设立了三个节度使,形成四节度镇守西北边疆的局面。其中,河西节度使驻凉州(今甘肃武威),统辖凉、甘、肃、瓜、沙等州,大致相当于今河西走廊地区;陇右节度使大致设立于先天元年(712)十月以前,驻鄯州(今青海乐都),统辖鄯、秦、河、渭、兰、武、洮、岷、廓、叠、宕、成等州,主要是陇山以西、黄河以东一带;北庭节度使设立于先天二年(713),驻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统辖伊、西、北庭等州,相当于今天山东部一带;安西节度使设立于开元二年(714)以前,驻龟兹(今新疆库车),统辖龟兹、于阗、疏勒、焉耆,相当于今塔里木盆地一带。这些节度使承担着不同的战略职责,据《通典·州郡典》所载,河西节度使“断隔羌胡”,陇右节度使“以备西戎”,北庭节度使“防制突骑施、坚昆、斩啜”,安西节度使“抚宁西域”。这样,传统的陇右道实际上一分为四,形成四大军事区域。
唐代的西北诸节度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呢?如前所述,王永兴阐明了河西节度使与安西、北庭节度使之间的根据地与前沿据点关系,但却将陇右节度使排除在外。他认为河西、安西、北庭三节度涉及西北军事格局,朔方、河东涉及北疆,范阳、平卢涉及东北,陇右、剑南涉及西南。这是将陇右划入了不同的军事区域。李文才则将安西、北庭、朔方、陇右、河西共五个节度使归为西北战区。这是将朔方节度使与原陇右道四节度一并讨论。实际上,西北诸节度中河西节度使与陇右节度使关系极为密切,安西节度使与北庭节度使亦曾多次合并,较为鲜明地形成河陇与西域两大军事区域。
河西与陇右并称“河陇”,二节度驻地之间距离非常近,从鄯州至凉州只有五百里。河陇地区在祁连山至黄河一线直接面对吐蕃的军事威胁,故而河西节度与陇右节度时常协同采取军事行动。《资治通鉴》卷212唐玄宗开元九年(721)载:“河西、陇右节度大使郭知运卒。”可知至少在开元九年就有军将兼任河西、陇右两节度使,距离陇右节度使设立时间不远。此后,又有王君、盖嘉运、皇甫惟明、王忠嗣、哥舒翰等兼任河西、陇右节度,以协调两节度防范吐蕃。可知,在玄宗时期持续面对吐蕃威胁的情况下,河西与陇右的军事联系非常紧密,不能将他们划分入不同的军事格局。
安西节度与北庭节度,皆位于阳关、玉门关以西,葱岭以东,是传统上所称的“西域”地区。自玄宗初年设立之后,安西、北庭两节度经历了数次分合。开元十五年(727)前,安西、北庭曾合并为一,至开元十五年三月又分为两节度。开元十九年(731),合伊西、北庭二节度为安西四镇北庭经略节度使。开元二十二年(734)四月,北庭依旧分立为节度使。开元二十三年(735)十月,北庭又隶属安西四镇节度。直到开元二十九年(741),安西与北庭才固定为两节度。至天宝末年,封常清曾兼任安西、北庭两节度。安西节度使与北庭节度使的分合,是唐朝为应对西域局势而做出的持续调整。
可见,西北诸节度因其特殊的地理和军事格局,自然地分为河陇和西域两个区域。史念海因陇右道东西差异显著,即以沙州为界,将陇右道分为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这也与本文所述两大军事区域相合。至于朔方节度使,虽然其驻地从地理上说也是位于长安西北,但传统上其统辖地域隶属关内道,与河西、陇右虽然也在军事上互为响应,却没有更紧密的联系。只有在天宝五载(746),王忠嗣曾身兼朔方、河东、河西、陇右四节度使,但很快在天宝六载便被贬谪。此后未有节度使能兼统朔方与河陇,朔方也成为东、西两大藩镇集团争夺的焦点。故而本文讨论暂不涉及朔方问题,仅比较河陇与西域之格局关系。
二、重河陇、轻西域的西北格局
在河陇与西域两大军事区域之间,大致有重河陇而轻西域的格局。以下试从军力对比、节度使地位、河西对西域的临时兼统等方面论述。
(一)重河陇、轻西域的军力对比
河西、陇右节度的军事力量和军费投入远大于安西、北庭节度。《通典·州郡典》对各节度的兵、马、衣赐数量有详细记载,具体情况见表1。
从表中所示军力来看,安西与北庭节度更为接近,河西与陇右节度则大致相当。河陇地区两节度的兵马数是西域两节度的2—3倍,衣赐数量更是达到3—4倍,河陇相对于西域有明显的军力优势。实际上,安西与北庭节度使在整个“天宝十节度”中都属于兵力较少的,当时唐朝的边疆兵力主要集中在河西、陇右、河东、范阳等节度使。与西北的兵力格局类似的是,东北面属于河北道范围的范阳与平卢节度使,也有着轻重之别,传统的边疆政治、经济中心幽州的军事力量更强。
此外,《通典·食货典》载有另一种稍详细的军费开支的统计,涉及西北诸节度的部分(详见表2)。
所谓“籴米粟”当是与和籴有关,而“给衣”或是按季直接发给兵士衣装布。可以看到,西北诸节度的“费籴米粟”与“给衣”两项之和,就等于前表“衣赐”的数量,可知《通典·州郡典》所谓“衣赐”可能就是由这两项相加而来。无论如何,就河陇两节度与西域两节度的对比来说,籴米粟与给衣的开支也是相差悬殊的。
除此之外,河陇与西域在军镇的设置数量上也有差距。《资治通鉴》卷215唐玄宗天宝元年(742)正月条载:
置十节度、经略使以备边。安西节度抚宁西域,统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镇……北庭节度防制突骑施、坚昆,统瀚海、天山、伊吾三军,屯伊、西二州之境……河西节度断隔吐蕃、突厥,统赤水、大斗、建康、宁寇、玉门、墨离、豆卢、新泉八军,张掖、交城、白亭三守捉……陇右节度备御吐蕃,统临洮、河源、白水、安人、振威、威戎、漠门、宁塞、积石、镇西十军,绥和、合川、平夷三守捉。
《通典》《元和郡县图志》《旧唐书》等所载与此略同,《资治通鉴》将其置于天宝元年,大致认为这反映的是唐玄宗开元至天宝初年的情况。需要注意的是,安西节度使所辖之四镇,实际都设有镇守军。据此,这一时期安西节度使有四军,北庭节度使有三军,河西节度使有八军,陇右节度使有十军。
又《新唐书·兵志》载:
赤水、大斗、白亭、豆卢、墨离、建康、宁寇、玉门、伊吾、天山军十,乌城等守捉十四,曰河西道。瀚海、清海、静塞军三,沙钵等守捉十,曰北庭道。……保大军一,鹰娑都督一,兰城等守捉八,曰安西道。镇西、天成、振威、安人、绥戎、河源、白水、天威、榆林、临洮、莫门、神策、宁边、威胜、金天、武宁、曜武、积石军十八,平夷、绥和、合川守捉三,曰陇右道。
据《旧唐书·代宗纪》载,北庭的静塞军设置于大历六年(771)九月,可推知此处的记载可能是晚至安史之乱后的西北诸节度的情况。伊吾、天山二军显然一直是属于北庭道,则河西节度使还是八军,北庭节度使则增加为五军。这大致是因为安史之乱后,河西逐步被吐蕃占领,不会再新设军镇,北庭则坚守至德宗贞元年间。而陇右在被吐蕃逐步蚕食之前,可能已经进一步增加为十八军。至少从《新唐书》此处的记载看,河陇地区最终的军镇数量还是要远多于西域地区。节度使时代,军镇是各节度使最基本的军事力量,军镇数量的多少也可以看出节度使实力的强弱。
(二)重河陇、轻西域的节度使地位
河陇与西域地区节度使本身地位的不同,也直接反映出重河陇、轻西域的格局。
首先,安西、北庭的军政长官立功后常迁转至河陇任节度使。①郭虔瓘。开元二年二月,突厥默啜可汗之子同俄特勤围攻北庭,北庭都护郭虔瓘设伏击杀同俄特勤,迫使突厥撤兵。玄宗下诏褒奖,进封郭虔瓘为太原郡开国公。《资治通鉴》唐玄宗开元二年七月壬寅载:“以北庭都护郭虔瓘为凉州刺史、河西诸军州节度使。”显然是在郭虔瓘立功后不久,玄宗有意将其调至河西任节度使,不过郁贤皓、孟凡人等据河西节度使杨执一墓志判断,郭虔瓘并未实际赴任。②郭知运。开元二年郭虔瓘破突厥时,时任伊州刺史兼伊吾军使的郭知运同样立有战功,被玄宗下诏褒奖。同年秋,吐蕃侵扰陇右,郭知运随即被调往陇右,之后出任鄯州都督、陇右诸军节度大使。③盖嘉运。开元二十七年(739)七月,碛西节度使盖嘉运擒获突骑施可汗吐火仙,威震西域。开元二十八年(740)三月,盖嘉运入朝献捷,《资治通鉴》载:“上嘉盖嘉运之功,以为河西、陇右节度使,使之经略吐蕃。”④高仙芝。天宝年间,高仙芝任安西节度使,屡立战功。《资治通鉴》载:“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入朝,献所擒突骑施可汗、吐蕃酋长、石国王、朅师王。加仙芝开府仪同三司。寻以仙芝为河西节度使,代安思顺;思顺讽群胡割耳剺面请留己,制复留思顺于河西。”玄宗同样是想将高仙芝调任河西,但安思顺使用巧计显示其在凉州胡人中的威望,高仙芝才未能赴任。⑤杨预。《文苑英华》卷917载杨炎撰《四镇节度副使右金吾大将军杨公神道碑》有:“嗣子预,有霸王之略,好倜傥之奇。初以右武卫郎将见于行在,天子美其谈说,问以中兴。遂西聚铁关之兵,北税坚昆之马,起日城,开天郎,特拜左卫将军兼瓜州都督关西兵马使,又迁伊西北庭都护,策茂勋也。”安史之乱后中原动荡,急需援军平叛,杨预因聚集兵马有功,自瓜州调任北庭。《大唐都督杨公纪德颂》亦称其自“河西副持节”除“伊、西、庭节度等使,摄御史中丞”。又,敦煌P.4698文书有“使太常卿兼御史大夫杨”,此处的“使”为河西节度使,大致杨预此时又调任河西节度使,所带宪衔也从御史中丞升为御史大夫。⑥杨志烈。根据吐鲁番出土《唐宝应元年(762)五月节度使衙榜西州文》,杨志烈此时尚为北庭节度使。又据《旧唐书·吐蕃传》所载,广德元年(763)吐蕃自长安退兵后围攻凤翔,“会镇西节度兼御史中丞马璘领精骑千余自河西救杨志烈回,引兵入城”。可知,至晚在广德元年初,杨志烈已调任河西节度使。以上诸位节度都是自西域调任河陇任节度使,特别是盖嘉运调任时《资治通鉴》提到“上嘉盖嘉运之功”云云,可见自西域调任河陇是一种褒奖。这也说明河陇在西北军事格局中处于相对重要的位置。
其次,河陇地区节度使更接近唐廷的权力中枢。河西先后有萧嵩和牛仙客两位节度使因在河西的功绩而升任宰相。开元十五年,河西发生节度使王君遇害事件,史载“玄宗以君勇将无谋,果及于难,择堪边任者,乃以嵩为兵部尙书、河西节度使,判凉州事。”萧嵩任河西节度使后,迅速稳定了局势,与陇右节度使张志亮合力攻克吐蕃大莫门城,又遣将大胜吐蕃于祁连城。开元十六年(728)十一月,萧嵩便入朝担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次年,萧嵩更是出任中书令,成为实际上的宰相。他能获得玄宗青睐,无疑与在河西的战功有密切关联。萧嵩入相后,多次举荐牛仙客,最终由牛仙客接任河西节度使。牛仙客在河西多年,直到开元二十四年(736)秋才转任朔方,继任的河西节度使崔希逸上报朝廷,说“仙客在河西节度时,省用所积巨万”,得到玄宗的认可。于是在当年十一月,牛仙客任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仍知门下事,也成为宰相。牛仙客为相时最大的功绩是在关中推行和籴制度,解决了关中缺粮的问题,一般认为这是借鉴了在西北地区行之有效的经验。而玄宗时期的权相李林甫更是在开元二十六年(738)二月遥领陇右节度使,五月又遥领河西节度使,直到天宝初年才停知节度事。天宝五载开始兼任河西、陇右节度使的皇甫惟明,虽然并未入相,但因与太子过从甚密,被李林甫检举贬谪。西域地区的安西、北庭节度使,则鲜有出入朝廷中枢者,目前仅见碛西副大都护杜暹于开元十六年入相。即便如天宝年间著名的节度使高仙芝、封常清,也没有获得进入权力中枢的机会。这与唐玄宗时期主要敌手为河陇方向的吐蕃,而西域地区统治相对稳定多少有些关系,但还是能体现出河陇与西域节度使地位的差别。
(三)河西对西域的临时兼统
在战事紧急情况下,曾出现河西军政长官以不同形式统辖或监督西域军事。开元二十二年,唐朝置“十道采访处置使”,实际为十五道,其中“太仆卿兼判凉州都督、持节河西节度等副大使牛仙客为河西道采访使”,“秦州刺史裴敦复为陇右道采访使”。此前的陇右道也就被划分为河西与陇右两个采访使区域,陇右道采访使大致就应当是陇右节度使的范围,而河西道采访使则是由河西节度使副大使牛仙客兼任,其统辖范围除了河西节度使辖区,也远及西域。《张九龄集》卷12所载《敕河西节度副大使牛仙客书》云:
突骑施连岁犯边,凶恶如此,若不威服,只长寇仇。……卿可于河西诸军州,拣练骁雄五千人,即赴安西,受王斛斯分部;朕当发遣十八年安西应替五千四百八十人,与彼相续,足得成师。……已敕盖嘉运与王斛斯,审量事宜,临时为计。既为卿探访所管,亦宜随要指麾。兼有别敕发三万人,此但声援而已,可大张威势,远使震慑。又恐安西资用之乏,卿可于凉府将二十万段物往安西,令随事支拟,及充宴赐。朕则续支送凉州云云。
此敕时间大致在开元二十三年(735),当时突骑施侵犯安西、北庭诸州府,唐玄宗除了不断敦促安西节度使王斛斯与北庭都护盖嘉运商量应对外,也敕令河西的牛仙客予以接应。特别是其中提到“既为卿探(采)访所管,亦宜随要指麾”云云,联系前文提到牛仙客刚刚于开元二十二年就任河西道采访处置使,可知此时安西、北庭也在其采访监察之下,涉及紧急军务也可以由当道采访使指挥协调。王永兴据此提出,河西节度使在西北军事格局中处于指挥督察地位。然而此说并不确切,因为执行督察职责的实际上是采访使,只不过此时是有河西节度副大使牛仙客来担任河西道采访使,就河西节度使本身而言,不能说已经处于都统安西、北庭的位置。不过采访使设在河西,还是说明了河西的重要地位。
安史之乱后,唐朝又一度设“河已西副元帅”。敦煌P.2942判集文书中有《伊西庭留后周逸构突厥煞使主兼矫诏河已西副元帅》,提到“副帅巡内征兵,行至长泉遇害,军将亲观事迹,近到沙州具陈”云云,该判集又有《差郑支使往四镇索救援河西兵马一万人判》。此河已西副元帅应即河西节度使杨志烈,当时凉州已经被吐蕃攻陷,杨志烈赴北庭征兵但不幸遇害,此后河西又向安西四镇征兵。根据判文大致可以推知,由河西节度使兼任的河已西副元帅可以兼统河西、安西、北庭三节度,这大致是为了应对安史之乱后的特殊形势而进行的临时性调整。但很快河西诸州皆陷于吐蕃,河西节度使名存实亡,河已西副元帅也不见于史书。
总之,从特殊时期的监督统辖关系、军事力量和军费投入的悬殊对比以及节度使的流动方向等几个方面来看,唐代的西北军事布局确实存在重河陇、轻西域的差序格局。当然这里说的轻重只是相对概念,实际上唐朝十分重视西域的开拓与经营,如果进行纵向的时代对比,可以说唐朝在西域的军力部署与资源投入远超汉晋时期,从而保证其在安西、北庭地区建立起百余年的坚实统治。只不过从横向的地域对比来说,唐朝在西域的力量和投入显然要轻于河陇。
三、重河陇、轻西域格局的成因与作用
重河陇、轻西域差序格局的形成,受地理、军事和行政等多种因素影响,是唐朝为解决西北边疆经营问题而采取的布局。
首先,地理远近与交通能力限制是决定差序格局的根本因素。据《通典·州郡典》所载,鄯州去西京(长安)一千九百九十三里,去东京(洛阳)二千七百四十九里;凉州去西京二千一十里,去东京二千八百七十里;北庭都护府去西京六千一百三十里,去东京六千八百七十六里;安西都护府去西京七千六百里,去东京八千三百三十里。可见,从唐朝两京到安西、北庭两都护府的距离,大致也是到河陇核心区域凉州、鄯州距离的3—4倍。而且从地理上看,从两京出发必然要先经过河陇地区才能到达西域,可想而知,从内地调往西北的物资也必然先聚集在河陇,再中转运往西域。据《仪凤三年十月度支奏抄·四年金部符》,早在高宗时期,就有大量布帛从凉州中转运往瓜州、伊州。节度使时代恐怕也是如此,如前述开元年间《敕河西节度副大使牛仙客书》中便载有:“又恐安西资用之乏,卿可于凉府将二十万段物往安西,令随事支拟,及充宴赐。朕则续支送凉州云云。”这是玄宗指示河西节度使为安西提供物资保障,同样是从凉州中转调发。值得注意的是,节度使时代唐朝的边防制度从少量驻军的镇戍体制转变为大规模驻军的军镇体制,西北地区也是如此,即便安西、北庭总兵力也只在2万—3万,但相比此前也有了大幅增加。军需的转运也成为唐朝极大的负担,除了鼓励驻军屯田、和籴外,唐朝也依靠客商向西域输送布帛。《唐会要》载:“(开元)十二年(724)十月,除王君,又加长行转运使,自后遂为定额也。”西北地区又设立了专门的“长行转运使”,以统筹物资运输。张籍《凉州词》中所谓“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大致就是描述这种场景。在这样的地理和运输格局下,距离两京更近的河陇,必然适合屯聚更多的军事力量,而遥远的西域能维持现有规模已然不易。
其次,盛唐时期西北边疆的地缘军事形势影响了差序格局的形成。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提出,唐朝“全国重心本在西北一隅,而吐蕃盛强延及二百年之久。故当时唐代中国极盛之时,已不能不于东北方面采取维持现状之消极政略,而竭全国之武力财力积极进取,以开拓西方边境,统治中央亚细亚,借保关陇的安全为国策也”。此处虽然在论述开拓西域的重要性,但西域仍只是关陇的屏障。如果反过来从西域看关陇,显然关陇比西域更重要,可以说河陇地区是保卫关中的第一屏障,西域只是更外围。安史之乱后河陇被吐蕃占据,唐朝只能在凤翔至灵州一线防御,关中随时受到威胁,代宗时甚至一度被吐蕃攻陷长安。由此也可见关陇的地位。除此之外,河西还承担着“隔断羌胡”的重要作用。河西走廊深入西北,自凉州以西数州一字排开,控扼着狭长的地带,南面是青藏高原的吐蕃,北面则是草原的突厥。凉州夹在南北之间,受到来自两边的侵扰,这从客观上体现出凉州具有南北交通中介的重要性。唐朝也必然在河陇设重兵,保护漫长而缺乏纵深的防线。
最后,河陇与西域地区经济与人力资源的巨大差距也是形成差序格局的重要因素。河陇自汉代以来就是中原王朝持续经营的地区,北朝末年以来陇右贵族亦是所谓“关陇集团”的重要成员。唐代随着丝绸之路贸易的大发展,陇右更是成为富庶之地。《明皇杂录》称“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这当然有夸大的成分,而且可能主要描述的是陇右道东部的情况。若以阳关、玉门关为界,陇右道东部(即本文所谓河陇地区)领18州,而陇右道西部(即本文所谓西域地区)仅有3个正州以及4个羁縻都督府。至于户口,《元和郡县图志》载有开元时的诸州户数,《新唐书·地理志》则载有天宝时的诸州户口。此外,敦煌写本《天宝十道录》载有安西所辖羁縻都督府的户数。具体见表3。
就相对完整的天宝户数来看,陇右道东部共有102431户,西部共有36497户。河陇地区无论从人口数量还是人口密度来说,在唐朝州县中都不算多,但相对于西域地区则优势明显,唐朝统治下河陇地区的户数是西域地区的2.8倍。西域地区人力较少的状况显然会对唐朝在当地的统治产生一定影响,张广达即指出,即便是人口最多的西州在建立之初也面临人口紧张的问题。这种经济与人力资源的显著差别,使得西域能够为驻军提供的经济与人力保障远远不如河陇。就两个地区之间的资源调配来说,河陇甚至直接为西域提供大量支持。除了上文提到的物资转运外,更有相当数量的河陇兵士在西域从军,成为构成西域军事力量的组成部分。据《唐开元四年(716)李慈艺告身》,当时北庭的瀚海军中有来自河西瓜州和甘州的兵士。另据《唐景云二年张君义勋告》,安西镇守军中有来自沙州、秦州、甘州、凉州、肃州、鄯州、岷州、兰州的兵士。P.2625《敦煌名族志》则记载,出身敦煌阴氏家族的阴嗣监就曾任“北庭副大都护、瀚海军使兼营田支度等使”。西域相比于河陇无疑更加依赖中原的物资与人员支持,结合前文所属的地理与运输问题,就会促成明显的军事布局差异。
当然这种差序格局也有利于唐朝对遥远边疆的控制。在古代运输能力有限的情况下,自关陇向西域阶级推进,无疑是一个更稳妥的方案。一方面,安西、北庭节度使的兵力虽然不如河陇,但也足够完成常规的军事任务。玄宗时期唐朝在西域逐渐取得了对吐蕃和突骑施的战略优势,如开元二十七年(739)碛西节度使盖嘉运擒突骑施可汗吐火仙,安西副都护、四镇都知兵马使高仙芝攻破小勃律,擒其王及吐蕃公主等等,显然都是以安西、北庭节度使的驻军为主力完成的。另一方面,当西域情势危急时,也可以得到后方河陇或中原的有效支持。如前述《敕河西节度副大使牛仙客书》,就涉及筹划从河西调拨支援西域。这样,唐朝不用在更远的安西、北庭投入等同于河陇的军事和经济力量,也能维持边疆的稳定,即便就国力鼎盛的盛唐来说,这也是一种适合持久经营的方略。
四、余 论
总之,河陇与西域地区诸节度使的关系,是考察唐朝边疆治理体系的重要视角。唐代的陇右、河西、北庭、安西等西北诸节度使非完全对等,河西、陇右节度的军事力量和军费投入远大于安西、北庭节度,河陇地区节度使更加接近唐廷的权力中枢,河西军政长官也曾临时统辖或监督西域。由此来看,唐代的西北军事布局存在重河陇、轻西域的差序格局。
我们可以将重河陇、轻西域的西北诸节度差序格局,看作是一种“重内轻外”的边疆秩序建构。在传统的中央与地方研究视角下,学界习惯于讨论节度使时代“外重内轻”的全国格局,即唐朝重要的军事力量都集中在边疆,财政也向节度使倾斜,由此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这固然是解释玄宗时期央地关系的一个重要路径,但如果观察西北诸节度的布局细节的话,就会发现就边疆本身来说,唐朝还是有从内到外的一种差序设计,即接近政治核心区的河陇地位更加重要。这实际上也符合唐朝长期存在的一种边疆观念,从太宗时代的魏徵、褚遂良,到武周时期的狄仁杰,都曾提出为中原民生而放弃经营西域的主张。如褚遂良所言:“此河西者方以腹心,彼高昌者他人手足,岂得糜费中华,以事无用?”显然在褚遂良看来,河西比西域更加重要。同样在持续经营西域的主张中也蕴含着稳定西域以保全河陇的理念。例如,崔融在《拔四镇议》说:“西域动,自然威临南羌,南羌乐祸,必以封豕助虐。蛇豕交连,则河西危,河西危,则不得救。”这很形象地描述了西域与河西的战略关系。可见,在传统的“外重内轻”范式之外,也可以从更多侧面来观察节度使时代的天下秩序建构。
从唐代西北诸节度的视角,可以看到唐朝国家治理边疆策略的一个侧面。这也是唐代天下秩序的一种体现股票融资费用,从太宗时唐朝就建构起州县—边州—羁縻府州的差序格局,西北节度使的轻重差异也是这样一种天下模式的演化。表面上的差异性,实际可以成为维持统一性的有效途径。
发布于:江苏省
